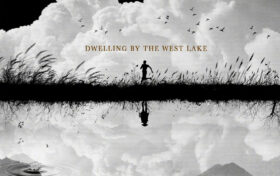《花漾女子》是非典型的女性复仇电影,它选择不走过往类型的套路,不稳固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它让你观看凯西的行动时直觉冒出她太冒险了、女性最好不要半夜出门,但凯西用行动告诉你,为什么不打破这种规则?

《花漾女子》是一部非典型的女性复仇电影,它选择不走过往类型的套路──刻画纯真的女性受尽身心痛苦与压迫之后,拿起刀、拿起枪展开一系列对男性的暴力复仇,如《追杀比尔》或是更早以前《我唾弃你的坟墓 (1978)》。它们美其名为女性复仇,但故事结构与传递的讯息,都不脱离女性因为生理柔弱或情感柔弱成为弱者与受害者,当女性以暴制暴及化身冷漠的复仇者,站上比加害者力量更强大的位置后,当加害的男性被毁灭与得到痛苦,她们的正义才得以伸张。
这一贯复仇思维其实稳固的是弱肉强食的合理性,让人不知不觉全盘接受了这个世界与这个社会就该是如此运行,更进一步来说,这种弱肉强食形成了弱者应该要懂得保护自己,远离强者带来的危险的认知观点。有趣的是,这类概念我们都不陌生并随处可见,就像遇到大车退三步或趋吉避凶或女性最好不要半夜出门,毕竟弱肉强食主宰的社会不会反过来思考大车遇到人应该退三步或男性最好不要半夜出门。

《花漾女子》剧照
《花漾女子》的编导艾莫芮德芬诺(Emerald Fennell)从电影第一幕、第一个画面就不断试图翻转过往媒体与电影千篇一律(不自觉)传播的观点,松动与挑战观者的既定认知,且时时刻刻与观者内心冒出的声音对质。艾莫芮德芬诺以夜店中凝视男性的胯下、扭动的肚子与上身,来翻转过去电影惯性以凝视女性胸部、身体曲线或外貌来观看电影中女性的角色。艾莫芮德芬诺另一个挑战,是在捡尸的男性选角上,选择大众认为这个看起来人很好他不会捡尸的形像,如亚当布洛迪、山姆理查森等。他们都趁著凯西看起来无力反抗的时候,将她带回家。
随故事揭露,凯莉墨里根饰演的凯西原来是装作喝醉再假装被捡尸,待男性要行动时,突然清醒给那些男人反扑。电影在此埋下悬念,最先的剪辑与她脚边的番茄酱,都会给观众制造凯西用暴力让那些男人得到了教训,但随著电影愈演到尾声,观众会察觉凯西任何一个复仇计画,都没有实际以暴力的方式伤害任何人。
凯西不断假装喝醉被捡尸,真正的目的如她对其中一个黑人男性所做,破坏他们的好事,让他们吃过一次闷亏懂得害怕,粉碎他们自认自己是强者的想法,就能让强弱关系失衡。而对于观众来说,观看凯西假装被捡尸过程也不是容易的,因为观者会不自觉向凯西投射,浮出弱者挑衅强者的可怕遭遇,但艾莫芮德芬诺一次次利用这个结构,让凯莉墨里根饰演的凯西,静静地几乎以表现双方是平等力量的姿态,脸上没有惧色的与男性僵持。
在工地被言语骚扰时,甚至被黑人男性想以力量吓唬时,凯西反而都让对方认清,她不是他们头脑里以为的弱者,翻转了整个情势,让男性无法轻易认为自己是强者。唯一,凯西略显懊悔使用暴力的时刻,是在公路下车拿著球棒吓到另一台卡车的时候,因为这让她感到自己变得和那些人一样。

编导艾莫芮德芬诺另一巧思跳开了女性复仇电影的套路,拒绝利用痛苦来剥削电影中的女性角色,选择让电影中被性侵的女主角之一妮娜已死,并借着凯西以另一种形式重现妮娜的困境在观众眼前。换句话说,编导不选择妮娜作为故事主角,是替观者尤其是女性观众拉开与妮娜的距离,让整起事件不会承载着妮娜痛苦的情感过重,使得故事变得聚焦于个人,反而失去理解整个社会才是加大妮娜痛苦的主因。
而全片最震撼一幕,是凯西反被艾尔以枕头窒息,艾莫芮德芬诺特别安排的镜头让我们联想了性侵与谋杀的相似;值得玩味是,艾莫芮德芬诺想必清楚观众内心都会希望凯西不要动了,而偏偏凯西一样在最后不愿屈服于弱肉强食的认知,她以她独特的方式来换回社会的正义。

艾莫芮德芬诺有意识在《花漾女子》中不放入任何一幕女性裸露或满足窥视的镜头,也拒绝让凯西成为皮肤紧致、脸上涂妆、减龄、纯真甜美的完美模样,一方面观众能从凯西的姿态与状态同理妮娜所受到的伤害;另一方面,对于未来不存希望、已经不愿与他人有多余连结的凯西而言,没有什么理由保持自己像女神般被观看、被赏心悦目。
艺术能映照出社会的样貌,让人们去从中思辨与意识究竟发了什么事,《花漾女子》试图拉出距离,让人们思索我们怎么认知我们的社会,并从凯西的复仇行动中理解我们或许也能有不一样的行动。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