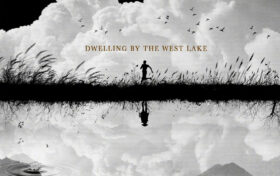去年读小说《刺杀小说家》时顺便搜了一下同名电影的卡司,当时在想,杨幂能演啥呢,果然,幂姐在银幕上面无表情地展示着黑白西装,推动着可有可无的情节,是一堆男人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当然,这部电影别无选择,它烙印着“路阳”“特效大制作”“3DIMAX”的标签,正在与贺岁档的其他商业制作激烈逐鹿。

当“商业片”成为一种电影类型时,小说作者双雪涛带着他的故事登场了。他的另一个故事《平原上的摩西》将在不久的将来登上大银幕,我们可以期待地说,是一部“文艺片”。在图书市场,他最近的小说集得到了知名出版社的青睐,屡登电商和实体书店的各类畅销榜单。在文学界,他获得了某种承认,得到了一个青年作家能够肩负的声望。这些多重意义上的成功印证着我们对故事的饥渴。

这种渴望一度被压抑,在“小时代“的光芒下成为一种难言的症结。在艺术电影被彻底逐出影院之后,资本终于开始不安地寻觅一个像模像样的故事,从同代的文学中汲取灵韵。双雪涛的登场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与之参照的还有青年作者任晓雯的作品《阳台上》,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他的作品具有改编成悬疑类型片的潜质,天然地亲和如今观众的娱乐口味,近年来,风行一时的悬疑类电影《唐人街探案》《误杀》《少年的你》,连同以《隐秘的角落》为代表的爱奇艺迷雾剧场,构成了大陆文化工业的一道风景线。
与双雪涛的其他作品不同,《刺杀小说家》的文本中具有大量异时空的文化符号和别开生面的战斗场景,这无意间又迎合了“大场面”“大制作”的技术制作惯性,近乎必然的在电影中升级成一处更为驳杂肆意的文化空间:傩面、火龙、坊市、赤发鬼,一切冠以虚构架空之名,为餍足观众的眼球提供了又一处奇景。文化工业对《刺杀小说家》的选择,既是对所谓“优质”类型片的无限复制,也是对视觉奇观的又一次生产和确认。这看似文学的突围,却始终缠绕着商业的梦魇。
小说讲了两个事儿,弑神和互文。我没有重读小说,对此处的互文不做评价,这是一个不断被理论家们讨论的问题,我只记得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作者在创作时的思想历险。而我也无法界说小说中要弑的神究竟是什么,因为作者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符号乱序地、杂糅地调用,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留白,使文本无法锚定于现实的历史问题。与小说家创作时的紧张感共振,弑神故事似是而非地表露出对政治权力的敏感,又或者,它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躯壳,只为满足小说家用虚构改写现实的快慰。

而双雪涛毕竟是一位当代作家,路阳毕竟是一位当代导演,我更关注从小说到电影,两大主题有何新的演绎。真正促使我写下这篇评论的是电影对“弑神”的明确界定,如果说小说中赤发鬼的象征意味不甚明晰,那么电影几乎是以一种近乎直白地方式指示了要屠戮的“新神”。在路空文的word文档出现的刹那,小说世界彻底,甚至不加变形地服从于现实世界,与赤发鬼对应的李沐,则是在电影一开头就明确设定为一个跨国垄断集团的老板,一个某种能“购买”用户时间的APP的拥有者,一个用全息影像发表演讲的煽动者。要杀的“新神”具身为渐趋或已经形成垄断的各大平台(以GAFAM,BAT为代表),集成了席卷全球的资本、数字技术以及与权力的深度合谋。更明确的例证是电影开篇关宁通过界面酷似微信的“神灯”APP与他人通信;李沐在演讲中提及“神灯”可以“制造时间”,让一小时能做二十件事;阿拉丁公司能肆意获取用户的隐私以实现监控和数据分析。
而这一命题仿佛一支哑火的手枪,在提出之后迅速沦为脆弱且孤立的所指。庸俗的寻女、替父报仇情节接管了接下来的现实世界,无法与“神何以至此”“如何弑神”等更为现实的问题产生关联。又由于审查,电影彻底丧失了对政治权力批判的可能性,这使虚构的仿古世界无力接收历史的遗产,同时有意地回避了当今社会多元的权力中心。

于是,电影的另一大主题“互文”反而成了一种遮蔽。如果文本已经空洞无物,何必去关注无意义的互文?如果现实已经鲜血淋漓,又何以指望在虚构中获得精神胜利?与导演路阳同姓的路空文和与原著作者双雪涛同样背景(辽宁,银行柜员)的关宁在电影中写小说,而路阳和双雪涛在画外创作了整部电影,从白翰坊到江城再到银幕之外,他们创造了层叠的三个世界,又躲在镜头后,只留下了前两个。他们何尝不知“新神”李沐的结局不可能交代,“小说能改变世界”的幻想无法推导出“电影能改变世界”的现实,又是否能意识到再自恋的互文也无法回应自己提出的问题?
一个更深刻的悖论仍然存在,这部电影本身就是文化工业的产品,它所反抗的神,正是生产它的母体。那些弑神的画面,无疑由燃烧大量资金的特效涂抹而成;它憎恶的大而不倒的社交媒体,正在传播着海量的软文并掌控着它的票房和口碑;它用两个小时的愤怒与浪漫对抗的阿里巴巴,赫然以金主的身份出现在电影片头。它不得不妥协,那些不得已的搞笑台词和动作游戏,连同多余的特异功能和杨幂的戏码,最终痛击了它的幻梦。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