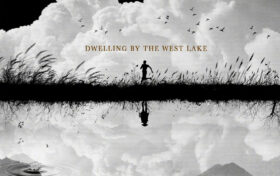“不知从哪一天起,总有一些东西让我激动不已。无论是天光将暗时街头拥挤的人流,还是阳光初照时小吃摊冒出的白汽,都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无论舒展还是扭曲着的生命都如此匆忙地在眼前浮动。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当他们走过时,我闻到了他们身上还有自己身上浓浓的汗味。当我们的气息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此达成沟通。”贾樟柯在个人电影手记中写道。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整个社会沉浸在破旧迎新的热烈氛围中,像影片中小勇这样下海经商,由曾经不光彩的小偷改头换面成为有头有脸的企业家的“手艺人”比比皆是,能为GDP做贡献便走上时代主流的舞台,而像小武这样念旧老实、不懂变通的人物成为社会的边缘角色。

有人搭上顺风车风光无限,有人无所适从活在过去。

小武是过去那种常见的“手艺人”,靠偷盗营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太笨,既没有头脑又没有真正的手艺,只能继续自己的老本行。然而小偷也有梦想。小武的心中,藏着一个豪气的英雄梦。

小武依然记得自己会在小勇结婚时送上二斤钱的承诺,作为“手艺人”的他,偷来二斤钱不请自来给小勇上礼。狭小的房间里两人上半身向后倾斜,曾经共患难的兄弟情义化为空气中无言的尴尬。小勇急于摆脱过去,与小武的交往经历也成了一段不光彩的回忆,后来的二斤钱被退回,并被嫌弃为“不光彩的钱”。

小武的承诺没有了兑现的途径。

小武后来在歌舞厅里遇见比自己高半个头的歌女韩梅梅,从此爱上韩梅梅,不善言辞、不会唱歌,在时代裹挟下茫然无措的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澡堂里一遍遍练习《心雨》,为的是以后能在歌舞厅和韩梅梅对唱。韩梅梅这个喜欢唱歌、被许多人夸赞“长得像明星”的女孩,在电话里用很高的声调兴奋地欺骗妈妈:自己在北京见导演,又准备签约拍戏了。后来在自己生病时,为小武唱《天空》,唱着唱着就哭了。两个孤独无依、有梦无法实现的人依靠在一起。小武因韩梅梅的提议买了传呼机,苦苦等待却一直没有收到韩梅梅的电话。去歌舞厅找韩梅梅时才知道她已经找到更好的归宿不告而别了。

虚幻的爱情如烟般消逝。

回到老家,贫困的一家人聊庄稼收成,商量为二儿子筹钱办婚礼。而小武百无聊赖地在一旁插不上话,显示了他在家中无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亲情在他心中仍有分量。他把自己原本要送给韩梅梅的金戒指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却为了冲门面把金戒指送给了二儿子未过门的媳妇,受到伤害的小武与母亲争执起来,一旁的老父亲听见拿起扫把要打这个败家子,最后甚至把他赶出了家门。小武倔强地对父亲说“不回来就不回来”,这时,镜头随着小武的眼睛看向自己的家,缓慢摇过贫穷但生养自己的家乡的每一处,与自己的家乡做最后的告别。

就这样,小武的亲情也没了安放之处。

回到城里,小武最后一个兄弟拆迁,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一旁的司机说“拆就拆了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旧的去了,新的在哪呢?从此小武的爱情、亲情和友情都在时代剧变中无处安放。

最后,在最后一次盗窃中小武的寻呼机响了,于是被抓了起来。警察郝老师带着小武出门,途中需要办点事,就用手铐把小武锁在外面,引来无数游人驻足围观。因为好奇驻足的游人,有的不明所以淡漠地看着,有人指指点点交谈起来,导演没有给此时的小武镜头,而那些犀利的目光却打在我脸上,打在所有观众的脸上,让人无法直视。这是小武的社会性死亡,是英雄梦的幻灭,也是最后尊严的无处安放。

在时光网纪念《小武》上映20周年的一篇特稿中,这样写道:一个小偷,一瞬的梦。电影就像是一幕关于深情的悲剧,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与“冲撞”即便过了20年,对照当下仍在急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这是一部茫然孤独的电影,一些美好的东西正从人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并且愈演愈烈。在物化的年代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渐渐变成商业联系,情感、命运越来越无处安放。

贾樟柯在《小武》的香港宣传海报上说:这是一部粗糙的影片。有人说贾樟柯的电影制作粗糙简陋,但无法阻挡那股属于一个时代鲜活的气息,其平凡真实的视角所赋予电影的力度,不仅接住了地气,更戳中了不知多少社会底层的人们那些迷茫无力的隐痛。对于这个评论我很赞同,唯一不能认同的是“制作粗糙简陋”。这种电影风格并非因为资金不足等问题所造成的,它反映了一种沉痛、有力的真实,贾樟柯说:“这是我的一种态度,是我对基层民间生活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验,我不能因为这种生活毫无浪漫色彩就不去正视它。具体到《小武》里的人物,我想表现他们在这样一种具体的条件下如何人性地存在。这是一种蒙昧、粗糙而又生机勃勃的存在,就像路边的杂草。”

说起贾樟柯的影片初衷,用他在一篇文章中的话:现在再去黄亭子,酒吧已经拆了,变成了土堆。这是一个比喻,一切皆可化尘而去。于是不得不抓紧电影,不为不朽,只为此中可以落泪。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