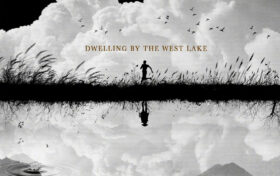藏族是我国西部的古老民族,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青藏高原高山大川密布、土地和水资源丰富,畜牧业发达,“羊”不仅为藏族人民的生活提供了许多物质保障,而且在影像中成为具有隐喻意义的“符码”。该片也以撞羊开始,在荒凉百里不见活物的地方窜出一只羊,营造了故事的荒诞感,也成为主人公精神信仰的外在表征。

羊是具有生命的实物,主人公撞羊之后产生了负罪感,通过为羊超度来消解这种负罪感。而这种负罪感的产生其实来自于主人公内心深层的信仰,坚信万物有灵、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佛教观念。撞羊后,搭载了要去复仇的杀手金巴,在货车这样一个密闭空间里,前面是对行人施舍的善,后面是死羊的血淋淋的恶,善恶交织,进而直击由“一只羊”的生命映射到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与人之信仰的探讨。

有人将《撞死了一只羊》理解为万玛才旦的刻意转型,实则不然,影片延续了以往电影的内核,只是通过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将视点更加聚焦到族群中个体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对自我精神的追寻。

相较于万玛才旦的前几部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撞死了一只羊》糅杂了回忆、梦境等元素,带来了更为独特的间离效果的体验,这样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观众的意义思考空间。混合了多种互动模式的非连贯现实,使得观众不连贯地从一个“现实”跳向另一个“现实”,以营造出叙事的荒诞感。正如导演所理解的那样,当现实的表达受到一些限制的时候,就需要找到另一种方法来表达。影片利用这种“想象的生活”的比喻来刻意引导观众将思绪聚焦在人物关系及其精神世界上。

“金巴”是电影中两人关系的叙事线索,也是个体探寻自我的象征符号。“金巴”是命运共生的,活佛让两人的行动主旨缠绕为一体。当司机金巴行驶在无人区,遇上杀手金巴时,真正的故事便开始了。或许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早已在暗中标好了页码。万玛才旦设置两人重名来投射两个金巴的内在牵连,司机问杀手叫什么名字,杀手回答叫金巴,这个名字是活佛起的。司机立马就对毫不起眼的“乞丐”提起了兴趣,也意识到他们的命运似乎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关联。此时的镜头充当了无声的叙述者,电影画面从两人中景全貌切换为一人一半的平行构图,人物被框在货车驾驶区域这样的闭塞空间,为接下来的镜像叙事埋下了伏笔。

辽阔的高原、荒芜的公路等是“金巴”的不安、焦虑及孤独的心境抒写。司机寻找杀手的过程中,导演运用一系列夸张变形的镜头及两个时空人物所处环境的一致性,如茶馆人物、窗外狗、玛扎牵着孩子走过的画面重复出现,利用这种多种互动模式的背景来烘托出故事的荒诞感,引导观众去将注意力集中在探索俩人的关系上,也正是通过这样的镜像人物描绘隐喻了镜像中探寻自我命运与精神的可能。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