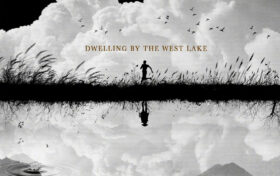根据契诃夫同名话剧改编的美国电影《海鸥》(The Seagull,2018)
《海鸥》的所有喜剧性在母亲阿尔卡基娜身上。她以她持续不老的魅力,像吸血鬼一般,永不餍足地吸取着他人的生命的精华。她是一个演员,仍旧受到城市资产阶级大众的热烈欢迎,仿佛她的魅力和姿色从来都不会谢幕,似乎有众粉丝以鲜血在持续地滋养灌溉她的生命。契诃夫对城市资产阶级大众也仅限于同情吧,他对于底层苦难的描述是惊心动魄的,但他将《海鸥》却标注为一出喜剧,让资产阶级艺术代表像个小丑一样肆意绽放。
母亲阿尔卡基娜是《春风不化雨》中的布鲁迪小姐,她同样认为,她还远远没有正式过了她的青春(Prime),还准备继续将她的生命献给她的观众,献给艺术。她说,“因为我工作,我用感情,我永远活动,而你呢(指乡下大庄园管家的女儿玛莎),你老待在一个地方,你不去生活……还有,我照例绝不操心未来。我永远也不想到老,也不想到死。”多么像永葆青春的中年人样板!不仅如此呢,她还在消耗着她身边的男人:她的儿子康斯坦丁,她的情人特里果林,她乡下大庄园的医生,还有她永远都在哀叹生命已经逝去的那个哥哥。
康斯坦丁有一番描述他母亲阿尔卡基娜的话:“她要生活,要爱,要穿鲜艳的上衣。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经常提醒她,说她已经不年轻了。可是,我不在她面前,她只有三十二岁;在我面前,她就是四十三了,这也就是她恨我的原因。她也知道我是反对目前这样的戏剧的。她却爱它,她认为她是在给人类、给神圣的艺术服务。可是我呢,我觉得,现代的舞台,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和一种格式。幕一拉开,角光一亮,在一间缺一面墙的屋子里,这些伟大的人才,这些神圣艺术的祭司们,就都给我们表演起人是怎样吃、怎样喝、怎样恋爱、怎样走路、又怎样穿上衣来了;当他们从那些庸俗的画面和语言里,拼着命要挤出一点点浅薄的、谁都晓得的说教来,这种说教,也只能适合家庭生活罢了;一千种不同的情形,他们只是永远演给我一种东西看,永远是那一种东西,永远还是那一种东西;——我一看见这些,就像莫泊桑躲开那座庸俗得把他的脑子都搅乱了的巴黎铁塔一样,拔腿就逃了。”

康斯坦丁(Billy Howle 饰演)
我们只能从她儿子康斯坦丁的口吻中,才能听出母亲的主流艺术是多么轻巧、投机和遭人厌恶。她应该是所有人谈论的“中心话题”,不然的话,她一旦找不到陶醉,就要“厌倦,恼怒”。人家要她唱歌,她拒绝了,因为唱歌不是她的强项。于是大家转了对象,要求年轻漂亮的新秀妮娜给大家唱一首歌。电影的下一个镜头,把妮娜满带希冀的脸和阿尔卡基娜的歌声拼接在一起。母亲阿尔卡基娜是有着嫉妒心的孔雀,却绝不允许她的儿子嫉妒她的情人,一个同样庸俗的成功小说作者特里果林。她在敖德萨一家银行存有七万卢布,可是你一向她提钱,她就哭穷。美国电影这样表述她临离开前,给女仆一整个卢布的情节:女仆脸上露出惊诧的表情,可是很快便转了鄙夷,因为她马上听说,这一个卢布是给他们三个仆人的。
母与子的那场交锋拍得好看极了!儿子康斯坦丁把哈姆雷特指责母亲的那套言辞说给她听:“对你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内心已经驯服,你不能把它叫做爱情!”美国导演Michael Mayer改编俄罗斯的戏剧,其中碰上了莎士比亚,让英国演员Billy Howle简直就如获至宝,Billy Howle的魅力立刻就闪耀起来了。当然,同时也很容易暴露康斯坦丁的恋母情结。法国导演Claude Miller根据《海鸥》改编的《小莉莉》中,对母子关系刻画得更加激烈而疯狂,带上了强烈的法国人的善感性。美国电影中的康斯坦丁要驯服得多,也更加忠于原著。康斯坦丁讽刺起母亲的虚荣来,每一句话都切中要害。电影的改编还提到了《麦克白》:尽管她声称前些日子才演了《麦克白》!儿子才不管那一套,问她是不是演的女巫。如果康斯坦丁没有自己的弱点被母亲抓住的话该多好,可是康斯坦丁是一个有着恋母情结的儿子呀。没有母亲的帮助,人家也会说他嫉妒呀,没有才华呀,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反正他这种处在寄人篱下并且不能远走高飞、最终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吃饭、还立志要做出一番成就的身无分文的年轻人来说,全身几乎是千疮百孔,可被人抓住小辫子,更何况是他自己的母亲。母亲向所有人都索要关注和感情,还不给人家钱。
阿尔卡基娜对情人特里果林说,“我是一个女人,也和任何普通女人一样,你不要跟我说你喜欢上了别的女人。”特里果林说:“只要你肯放我走,你就能成为与众不同的女人。”瞧瞧,多么俏皮和暗藏机锋。赖声川版的舞台剧《海鸥》,母亲阿尔卡基娜与情人小说家特里果林之间的关系就笑料百出。“你整个是属于我的!你这么有才气啊,你这么聪明啊,你是今天所有作家里最优秀的,你是俄罗斯的唯一的希望……你写得那么真诚,那么朴素,那么清新,幽默得恰到好处……你一笔就勾出一个人物或者一片风景的精华和性格来;你所写的人物,个个象活的一样。读你的作品,怎能不被热情所激动啊?你也许以为我这是在奉承你、谄媚你吧?那,你就看着我……看看我的眼睛……我的神色像说谎吗?你要明白,只有我才真正知道你的价值,只有我;跟你说实话的,也只有我,我亲爱的,我的宝贝……你还肯走吗?真的,你不抛弃我啦?”那年,我和两个朋友在国家大剧院看到这段,始终都在大笑,还惹得前座的女人侧目,好像我们过于不尊重艺术一样,可是,契诃夫和赖声川在明确表达着喜剧精神呀!
特里果林也注定离不开阿尔卡基娜,她像是用一系列咒语将他捕获,她只是用“你是我认为最有才华的作家”等等一系列恭维就把他拘束住了。妮娜是没有学会这套本事,她只懂得爱一个人,不懂得如何恭维。然后阿尔卡基娜对特里果林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留下来。我今天先走,一个星期以后,你再找我去。说起来,你何必要这么匆匆忙忙的呢?”她懂得在关键的时候强势,在无伤大雅的时候大方。
阿尔卡基娜永远都吸引医生的爱,但是永远都不能补偿他。她说她之所以年轻,是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停止工作,停止活着。她建议所有人都像她一样去做,可是大家都没有生活的资本呀!她把控了舞台那么多年,就像把控着庄园里所有人的人生一样。当她厌倦了,农忙时期没有马这种事情都几乎不能阻止她去莫斯科。她知道她永远比不上年轻鲜活的妮娜,可是她知道妮娜不是她的对手,毕竟一个年轻女孩子,光有感情不行,还要有钱才行呀!妮娜彻底被生活毁灭了,她,阿尔卡基娜,仍旧是莫斯科戏剧舞台上的明星。
阿尔卡基娜:而且,我还象一个英国人那么注重仪表。我永远叫自己整整齐齐的,就象大家常说的,无论是梳妆,无论是打扮,永远comme il faut(as the way it is)。我每逢出门,哪怕是只走到花园里来,你也永远看不见我穿着négligé(nightgown)或者没有梳头。能够叫我保持年轻的,就是因为我从来不让我自己成为一个不整洁的女人,从来不象别的女人那么马马虎虎。(两手叉着腰,在游戏场上走来走去)你看我,看上去象只小鸡那么活泼;我还能演十五岁的小姑娘!
阿尔卡基娜的这番话,让厨娘不淡定了。你看,连厨娘都知道她已经不再像是十五岁的小姑娘,恐怕没有知识的厨娘的智慧不限于此,她恐怕理解得更多,比方说,阿尔卡基娜并不是因为自己时尚才年轻,而是因为她在掌控着一切经济命脉,强行享用着众粉丝源源不断供应的鲜血,才这么年轻有活力的。她不愿意给哥哥钱,让他临死前去莫斯科;她不愿意给儿子,让他出国走一走,或许能找到自己写作的方向。

医生(中)

阿尔卡基娜(Annette Bening 饰演)
《海鸥》,是两个女人的戏,这是整出戏之所以是喜剧的基础。阿尔卡基娜和妮娜,尽管这两个女人并没有正面交锋。这两个女人掌控着男人们的爱情。阿尔卡基娜自然是嫉妒妮娜的,因为妮娜年轻、貌美,有才华,还吸引了她的儿子和她的情人的关注。可是,她是用一两句话,就把年轻的妮娜杀死的。她说,可怜的妮娜,她的母亲的财产归了她的父亲,她的父亲的财产也会给她的继母,没有妮娜一分钱。倘若妮娜继承了财产,恐怕阿尔卡基娜就死定了。
契诃夫是擅长省略掉那些曲折的人生故事的,就像妮娜离开自己的故乡,一面去努力做演员,一面和她崇拜的男人同居,后来她死掉了孩子,被男人抛弃,在演出中疲于奔命,越混越惨。她停止不了对特里果林的爱,她兴致勃勃地加入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队伍,和农民们坐一样的三等车厢,全国巡演。可是这些人生在契诃夫的笔下,只是由康斯坦丁两句话说出来的。然后我们集中听到的,是妮娜对于人生意义的叩问。我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生命是有意义的,那我们的一切苦难都应该是有偿的;如果生命是无意义的,那我们应该积极去享乐,而不是承受苦难。

妮娜与特里果林
不仅仅是妮娜,《海鸥》中所有的小人物,都感到巨大生命热情的浪费。这是契诃夫的单恋模式。当康斯坦丁狠心叫爱他的玛莎走开的时候,玛莎转过身来,也叫爱他的小学教员走开。比喜剧恐怖的是,玛莎选择嫁给了小学教员,就跳进了不幸福的宿命中。多么残酷的契诃夫,他将之称为喜剧。契诃夫笔下的所有人都在毫无缘由地不停地爱着一个人,没有爱的回报。他们爱得越深,越感到人生的浪费。而生活几乎无事到仿佛从来都没有发生变化。
电影采用了互文般修辞手法的倒叙,一开始阿尔卡基娜的回家是简略的,最后阿尔卡基娜的回家在补充着电影一开始的回家细节。他们是参差而连贯的。你可以理解成循环往复,也可以理解成互补。只是意义毫无例外的继续被消耗。
是时候作出反抗了。康斯坦丁第二次朝自己开枪,终于成功射杀自己。这时候镜头完全在母亲阿尔卡基娜的脸上停留。她那略带迷茫的表情,似乎在隐约感到不祥的到来。她是迷信的,像一切享乐主义者一样,任何细微的征兆,都会毫无疑问地指向恐怖的死亡。不过,以后再也没有人提醒她真实的年纪了,她可以永葆青春了,她准能够再继续活很多年,忙碌很多年,享受更多的美好。这只是我们的猜测,她面部表情上的象征意义上的虚无,直指俄罗斯社会的弊端和俄罗斯式的生命哲学。
讨论契诃夫,是逃避不开进化论出现后的世界观的。医生用进化论支撑的科学观,奋力地挽救着这个古老的俄罗斯。可是医生是多么渺小呀,无非是和几个女人偷偷情,觊觎着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的女主人。这种巨大的荒诞的喜剧性,就是两种世界观的割裂的结果。在康斯坦丁的实验戏剧中,表达着几百万年之后人类和历史的虚无。这恰巧也投合了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就像《三姐妹》中“俄罗斯有两个莫斯科大学”,这就意味着有两个俄罗斯!一个进化论的俄罗斯,一个传统东正教的俄罗斯。康斯坦丁和妮娜年轻的生命热情在持续被浪费,然后他们的命运选择也开始出现分歧。康斯坦丁不再继续忍耐下去了。
妮娜:人,狮子,鹰和鹧鸪,长着犄角的鹿,鹅,蜘蛛,居住在水中的无言的鱼,海盘车,和一切肉眼所看不见的生灵——总之,一切生命,一切,一切,都在完成它们凄惨的变化历程之后绝迹了……到现在,大地已经有千万年不再负荷着任何一个活的东西了,可怜的月亮徒然点着它的明灯。草地上,清晨不再扬起鹭鸶的长鸣,菩提树里再也听不见小金虫的低吟了。只有寒冷、空虚、凄凉。
所有生灵的肉体都已经化成了尘埃;都已经被那个永恒的物质力量变成了石头、水和浮云;它们的灵魂,都融合在一起,化成了一个。这个宇宙的灵魂,就是我……我啊……我觉得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和莎士比亚,拿破仑和最后一只蚂蝗的灵魂,都集中在我的身上。人类的理性和禽兽的本能,在我的身上结为一体了。我记得一切,一切,一切,这些生灵的每一个生命都重新在我身上活着。
阿尔卡基娜:(极小的声音)有点颓废派的味道。
特里波列夫:(请求地,带着指责的神色)妈妈!
妮娜:我孤独啊。每隔一百年,我才张嘴说话一次,可是,我的声音在空漠中凄凉地回响着,没有人听……而你们呢,惨白的火光啊,也不听听我的声音……沼泽里的腐水,靠近黎明时分,就把你们分娩出来,你们于是没有思想地、没有意志地、没有生命的脉搏地一直漂泊到黄昏。那个不朽的物质力量之父,撒旦,生怕你们重新获得生命,立刻就对你们,象对顽石和流水一样,不断地进行着原子的点化,于是,你们就永无休止地变化着。整个的宇宙里,除了精神,没有一样是固定的,不变的。
我,就像被投进空虚而深邃的井里的一个俘虏一般,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我是很清楚的,就是,在和撒旦,一切物质力量之主的一场残酷的斗争中,我会战胜,而且,在我胜利以后,物质和精神将会融化成为完美和谐的一体,而宇宙的自由将会开始统治一切。但是那个情景的实现,只能是一点一点的,必须经过千千万万年,等到月亮、灿烂的天狼星和大地都化成尘埃以后啊……在那以前,一切将只有恐怖……
没有必要刻意去理解这段戏中戏的真正含义,母亲阿尔卡基娜和这出戏中戏的碰撞是一出精彩的喜剧。

立陶宛OKT剧院《海鸥》中的康斯坦丁
电影对于这段戏中戏的改编,使用了投影配图和舞台表演双重形式,有很镜头感。母亲阿尔卡基娜在台下点评的关键词,什么“颓废派味道”呀,什么“恐怖”呀,就足以说明这段戏中戏的真正含义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生命,只有永恒,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恐怕就是这段戏中戏的样子。永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热爱生命的热情,呼之欲出。我们渴求人生意义的欲望,止不住地要爆发了。契诃夫让生命的享乐,直接嘲笑了永恒,尽管这两种人生方式,他一个都不赞成。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生命的被浪费。“到达永恒的和谐之前,一切将只有恐怖”的生活有什么好过的呢?而及时行乐、从来都不考虑以后的母亲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消费主义,损害了多少人宝贵的人生!
巨大的生命热情被浪费掉,是俄罗斯文学的母题。可是那些消耗别人生命以滋养自己的人物,从来没有《海鸥》中的母亲,这样成功过。只有母亲,感到自己在生活。其他人,都觉得人生毫无意义。难怪苏联时期,将契诃夫《脖子上的安娜》改编成了左派电影,说统治阶级将劳苦大众中最美好的东西(安娜)占有了去,而劳苦大众被迫流落街头,变得一无所有。契诃夫的这种人生意义的被剥夺,直接被苏联电影学去,将它翻译成一切美好都被剥夺。让我们听一听妮娜在她崇拜的作家特里果林面前的一番话吧:
妮娜:人的命运多么不同啊!有些人的生活是单调的、暗淡的,几乎拖都拖不下去;他们都一样,都是不幸的。又有些人呢,比如像你吧——这是一百万人里才有一个的,——就享受着一个有趣的、光明的、充满了意义的……生活。你真幸福……
特里果林:幸福,我吗?(耸肩)哼……你谈到名望,谈到幸福,谈到光明的、有趣的生活。可是,对于我,所有这些美丽的字句,就象是——请原谅我用这样一个名词吧——果子酱,对我毫无意义。
噢,那些艳羡别人的成功的人,和生活在成功中的人,都感觉不到幸福。契诃夫像迷路的康斯坦丁一样,没有找到除此之外的人生的意义,只好用喜剧来自嘲。就像剧本的开头,麦德维坚科问玛莎:“你为什么总是穿着黑衣裳?”玛莎说:“我给我的生活挂孝啊。我很不幸。”然后麦德维坚科就形容了一番自己的生活入不敷出,有多么悲惨。尽管理论上讲,贫穷的人也能幸福,然而应付起现实来,还是有些窘迫和慌张。这算什么喜剧呀?尤其是接下来关于“永恒与和谐”的戏剧就要徐徐拉开大幕。当没有希望的人,只剩下了“永恒与和谐”,这种自嘲是不是有些过于苦痛?难怪人们都将《海鸥》理解为悲剧。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