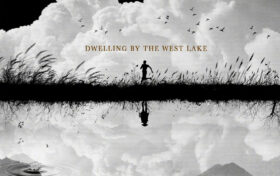万玛才旦导演的最新电影《气球》登陆院线,引发了不同面向的讨论。不同于万玛之前的电影,这部影片以女性为第一主角,展现了一出现实与信仰冲突导致的家庭矛盾。
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气球》故事的核心——生育问题,足以打动每一位女性。因为生理原因,生育是每一位女性都必须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即使选择不婚育,也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存在。因此,在这点上,所有的女性都是同盟军。

1、藏地生育往事
《气球》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卓嘎和丈夫达杰是藏地的普通牧民,他们和三个儿子以及达杰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作为家里唯一的女性,卓嘎不仅需要劳作,也承担着对家庭、家人的大部分照料工作。她也有隐秘的烦恼,丈夫性欲旺盛,而她怕再次怀孕,想去做结扎手术。
日子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着,生活里的小状况无非是家里的母羊年纪大了不能生仔要被卖掉,避孕套被贪玩的小儿子拿走当气球吹,结扎手术得等等看和村上的妇女一起做,或者是已经出家做尼姑的小姑子香曲卓玛心里还惦念着前男友……
在故事的前半段,卓嘎可谓标准的贤妻良母,她辅佐丈夫,照顾孩子和老人,还成功安排了卓玛和前男友见面,化解了未斩断的红尘。突然,卓嘎怀孕了,这个家庭也遭遇了危机。
面对已经有三个儿子的沉重生活负担以及超生会罚款的政策现实,卓嘎考虑拿掉肚子里的小孩。偏偏这时候,达杰的父亲去世,所有的人都认为卓嘎肚子里的孩子是老人家转世,这让她想拿掉孩子的愿望要面对信仰的拷问。
这时候,卓嘎的选择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她拿出自己的勇气,第一次反抗了丈夫。言语间,他们爆发了冲突,丈夫打了她一巴掌。卫生所的女医生说:“我们女人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不停地生孩子的。”
电影的结局是开放式的,卓嘎选择和卓玛去寺庙住一段时间,她可能需要信仰修补自己和丈夫的关系,也可能是去静静等待新生儿的降临。母亲离去后,小儿子们终于获得了真正的气球,但又很快失去,红色的气球随着风飘往很远的地方,每一个在电影中出现过的角色都看见了它。

2、女性的共情时刻
《气球》有意识地设定了两个女性角色,嫂子卓嘎和妹妹香曲卓玛。通过其他主人公的讲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妹妹出家的原因似乎与多年前恋爱失败有关。电影指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男性总是在无形中改变着女性的命运走向。
卓嘎和卓玛形成了一组镜像关系,卓嘎一开始以父权附庸的形象出现,她阻止了妹妹卓玛可能的越轨行为;而卓玛因为信仰,虽然并不认同嫂子的选择,却还是给予了善意的理解,两位女性的处境因此有了互文的对照意味。
其实,我们也很难不去同情电影里的丈夫达杰,尽管他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这个男人简单直接粗暴,他认为不能生育的母羊是无用的,也认为卓嘎想要拿掉孩子的想法是“妖女”才会有的。
在夫妻关系里,像所有传统的家庭一样,他们内外有别,避孕这种事,自然是卓嘎来处理。面对牧区计划生育政策的到来,达杰无所适从,他对妻子的伤害是无心的:一方面在父权制结构里没有自觉意识,一方面在粗粝生活的打磨下也失去了细腻的一面。
现实情况是,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环境中,男性因为体力优势,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因此他们也占据着家庭中的话语权,卓嘎们只能被迫处于“无声”的境地。当外部文明逐渐进入藏区,新的观念出现之后,卓嘎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女性的自我意识总是要受到各种打压而被层层折损,万玛给出了很多细节来展现这场意外怀孕本不应该发生。卓嘎对丈夫的性要求多少有点抗拒,她想要结扎,却需要排队,想要使用避孕套,却被儿子拿走;她的家境和受教育程度也让她无法通过卫生所之外的途径获得更好的避孕手段。这些压力很难说全部是因为达杰是一个坏丈夫造成的,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
可以说,卓嘎对生育的决定权是被一场“合谋”剥夺的。我们很难明确到底是哪一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她的遭遇显然是万千女性可能面临的困境的缩影。卓嘎在父权、母职和道德捆绑与薄弱的社会援助之间的挣扎,超越了藏地独特的文化环境,从而具有更普世的代表性。

3、电影中的生育问题及女性的反抗
大热的美剧《使女的故事》改编自著名作家阿斯特伍德的同名小说,虚幻了在不久的未来,因为世界被严重污染,出生率极低,部分地区经过革命建立起以男性为主导的集权社会。在这里,女性被当作财产,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则被当作“使女”,成为统治阶级的生育工具。

《使女的故事》

《地久天长》
一边是不想生育而必须生,一边是想生育而不可得。这些影视剧用戏剧化的方式展现了女性的身体是如何被工具化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因为子宫而消失了主体性,可谓对人权的莫大讽刺。甚至,因为生育的问题,曾有无数的女性惨死,有的是因为不能进行合法的流产而死在了黑诊所,有的则因为无法生育而被虐杀。
最近,山东发生的一起虐杀儿媳的案件,再一次把女性的生命权与生育权绑定在一起,仅仅因为结婚一年多没有怀孕,才20出头的方洋洋就被公婆和丈夫虐待致死。最可怕的是,这起案件爆发后,公婆分别获刑三年和两年两个月,丈夫获得缓刑,如此轻的量刑引发舆论热议,德州中院不得不发回重审。这起案件表明,即便在2020年的今天,父权制的作用方式依然是结构性的。

方洋洋在婚礼上
与此同时,不仅在偏远地区,在女性力量日渐被看见、被承认的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女性至今也依然无法摆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生育枷锁。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熟悉的样本,女主角金智英喜欢文学,也曾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生了孩子,她不得不退回家庭照料一切。丈夫也能够尽量体贴金智英,但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往往是被忽视的劳动,她感到自己的存在感消失了。
可以与之对比的是日剧《坡道上的家》,女主角产后一边要照料不断哭闹的孩子,一边还不断被婆婆和丈夫打击,她在患上产后抑郁之后精神恍惚,孩子溺毙在浴池里。

《坡道上的家》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