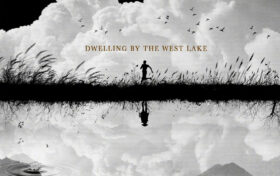第一次听说铁西区这个地方,是在高中的地理课上。那个时候,老师一手拿着卷子,一手指着多媒体的投影屏对我们说:
“铁西区这个地方,被称作东方鲁尔区,是当年东三省发展重工业的核心地带。可惜,现在你就算到沈阳的大街上去看,也没有几个人了。”

年少的时候,却是对“工业”、“地文”之类的大词颇感厌恶。直到最近离职,方能抽出大段时间拾遗。刚巧,前段时间798刚开了王兵摄影展,展出的是关于铁西区不少从未公开过的影像资料。种种机缘巧合凑在一起,我才把他的这部成名作提上片单的优先级。
《铁西区》分为3部,上映于2003年,那年我7岁,被非典闷在家里,有几分不用上学的快乐,也有几分对
一线抗击疫情的母亲的担忧。如此看来,17年也就不过一番轮回罢了。
站在这个节点上回顾,倒是有了许多别样的体会。
三部铁西区加在一起,时长超过9小时。
第一部开场,是长达7分钟的“幻影移动”镜头。昏沉的天光,晶白的雪地,镜头前蒙上一层水汽,随着火车,缓缓驶过铁西区的厂房和民居 。
《铁》这里选择这样的拍摄方式,其一或许是当年的拍摄条件限制,手持DV机,只能选用成本相对低廉的摄制手段,其二,也在无形中为整部《铁西区》奠下基调。
马克·卡曾斯曾在《电影史话》中评价这种手法,并援引了同样长达9小时的纪录片《浩劫》为例:克洛德·朗玆曼在《浩劫》中对于幻影移动的运用,使其具备了更多道德含义。
听其语气,是推崇备至。
而王兵所做,刚好是反蒙太奇,反“审判式凝思”的。在《工厂》当中,他近乎化身为绝对客观的他者视角,与拍摄对象不交流,不互动,甚至连剪辑都十分随意。光从美感上看,无疑是贫瘠的。但他却无意当中触及到了影像的另一重境界,那就是撤去所有人为干预,使得影像浑然一体。
工人们完全习惯了DV机的存在,集体生活的各种窘迫、龃龉,甚至是赤身裸体,都丝毫不避讳。这对于含蓄传统的上一代国人来说,实是了不得。当然,能达到这重境界,与导演在镜头外和工人们的熟稔也有很大关系。

有了真世相,才有真流露。第一部前半印象最深的段落,是一个小伙,在和工友们商量着怎么混来一张病假条。在当时,原则上不允许休假,医院盖章许可的病假申请算是个例外。 这样的情形下,能搞到医生的盖戳,似乎就成了门路和人脉的象征。
全年无休的工作模式,哪怕是对集体生产来说,也严苛得不尽人意。管中窥豹,你能看到时代的畸变。
那是怎样一个时代?
改革开放,全国经济大换血,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国有重工业基地。从70年代开始,铁西区就开始走向下坡。到了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率先破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倒闭的企业。
靠着余热,铁西工业区又挺了10多年。这就来到了影片拍摄的时间点,2000年春。
据当时在铁西上班的老员工回忆,当时每月工资也就一两百块,还经常连续几个月发不出来。30年的工龄,每年按500多块钱算,总共两万块钱,就算彻底买断,和厂子脱离关系了。
锤炼钢材的工业之火将熄,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再加上有人中饱私囊,即是大厦将倾。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大局势,往往是在野的小人物看得通透。

倒闭潮,下岗潮,朝潮朝落。本就破旧的车间休息室,变得兵荒马乱。大家都冲进来,拿走自己的心仪之物,就像旧社会的王府破败,小厮管家纷纷抱着值钱物件,树倒猢狲散。

只有小部分工人,能在这个节骨眼逃进疗养院,权且当作避世。他们在里面打牌、唱K、聚众看A片,仿佛生活在乌托邦里。
可就是这座乌托邦里,发生了3部《铁》中唯一的死亡事件。关于事件经过,几个人的谈话交代得语焉不详。大概意思是有个老工人,进水库摸虾的时候淹死了。
我对20年前的这场意外表示遗憾,却对这种春秋笔法的处理方式感到十分欣赏。
悬于整座城市的钢铁巨兽都已濒死,何况是渺小的个人呢?
第二部,名叫《艳粉街》。听到这个名字,你很难不往歪处上去想。但真正看到街景,就会放下那些暧昧的念头。无关风月,只是一片矮旧的平房。塑料袋、废石渣土、碎煤块、木柴,涨满了整条街道。

就是在这料峭的环境里,王兵讲述着火热的青春。以刘波为首的少年团体,十七八岁,正是逐渐步入成人社会的关头。他们整日游荡在大街小巷,无所事事,寻欢作乐。讨论讨论如何追到人家的姑娘,批改批改彼此的情书。
春心萌动,跟《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拍婆子、《牯岭街》里的泡miss、《美国往事》里的招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曾评价:与这些衰败的房子形成对比的正是这群十七、十八岁的少男少女,他们的青春、爱情、欲望、欢笑、嘻闹成为这个晦暗背景中的一抹亮色,仿佛是每天升腾在屋顶上的云彩。虽然他们无所事事地整天在堆满积雪与垃圾的社区里游荡,但他们的出现还是为这个沉沦中的街区带来对生命活力的希冀,他们代表着这个街区最有生命活力的群体。
关于此番情景,我还跟798王兵个展的负责人聊了一下。因为光看刘波等人的衣着体态,实在很难将之与“少年”划上等号。负责人告诉我,在那个年代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整个的生理状态也和当下的我们有很大不同。所以,便是不能以当今的标准去看待他们。
顺便提一句,从补足纪录片素材的角度看,这次展览最珍贵的,其实是刘波与当时追求的女孩张娜的合影。因为在片中,张娜从没露出过一张清晰的正脸。合影之时,两人颇为亲密。但据负责人讲述,后来他们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展览中的那张合影忘记照了,本以为片中也有同样的画面…
工业景观下独有的少年生态,唯一能与我们这代人挂靠起来的便是迷茫。片中,刘波跟好友唠着嗑,明明自己的未来都还没有着落,偏偏担心起别人的理想。好友遂带着脏字,笑着回应他:“啥理想啊,能当饭吃啊?”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放之四海皆准。
纯真、倔强,带着几分梦幻。这个时候,如同工厂的工人们一样,艳粉街的少年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拆迁。作为主要劳动力,四处奔忙干体力活不说,还得为使用面积、交换几类房源、添上多少补款等等问题精打细算。
少年口中宛如蛇蝎的房管所,与之不断地抗争,妥协,再抗争。这或许是他们首次与体制交手,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还将会有无数次。
垂垂老矣的工业之城在翻身,在死境之线上挣扎,生活在其肌理的少年也迅速成长。而真正引人好奇的问题是,他们会长成哪般模样?
直到今天,我仍旧相信艳粉街的青春才是大部分中国式青春的底色。论及生动活泼,他们的嬉笑怒骂比那所谓“后浪”宣言强出不知多少。
从影像水准来看,第三部最为粗糙。大量的夜景、微弱的光源、逼仄的空间,合着隆隆的铁轨声形成白噪音,有着非常强烈的催眠作用。可相对而言,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
王
兵曾在访谈上说,刚开始拿起相机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直到第一部《工厂》拍完,才有了想法。于是我们看到他记述的主体,由3间工厂,到主线人物,再到一个核心主角。
《铁路》2个小时,说到底是老杜一家的故事。他是所谓“特勤”,实则不过体制边缘的尴尬角色。每天都得跟正式的铁路员工打好关系,捡点煤渣,跟大儿子杜阳挤在一间上面施舍的小仓库里。就这么生活了20多年。

老杜也正经当过手艺人,跟父亲学了做熟食的厨艺。无奈被打上“投机倒把”,家产被抄。收留过一个比他小上15岁的盲流女青年,二人结婚生子后,老婆不甘困苦,离家出走,5年多没回来过。大家都知道老杜不容易,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老杜占点儿便宜,好赖能养活一家。
职工们讲情面,上面单位可不讲。厂子不创收,就得先拿你黑户开刀。自诩雷打不动的老杜被抓进看守所,小仓库也要被没收。只剩下杜阳在家,孤苦无依。
在镜头前面,他从编织袋里拿出塑料袋,大袋小袋层层迭迭,取出一摞全家人的合影。没说出两句话,泪水已经打湿了相片。
这是《铁西区》里记录在案的唯一一次流泪。
刚好这个时候,窗外的铃声响起。辨其音调,应是上课铃。几重语义混合,立马让眼前的这幕景象变得极具冲击力。在同龄孩子理应享受学生时代的天真浪漫之时,杜阳独自在家,默默垂泪,连明天的生计都尚且可知。反蒙太奇的客观纪实,在这一刻被打开了情感闸门,宣泄而出,让我的鼻头几近发酸。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这句话同样出自王兵。就创作母题而言,倒是与最近沸沸扬扬的《DAU》系列颇有类似。但二者间传递出来的张力却高下立判。只能说,虚拟的就是虚拟的,哪怕再极致,它仍旧是虚拟的。
我目前最喜欢的一部《DAU》,但它的冲击纯粹立足伦理层面
老杜被放出来以后,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每月赚得800多块钱,租了间更大更敞亮的房子。过年期间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宴请照顾过他的哥们。影片接近尾声,还走进来一位气表不凡的女性。按照老杜的语气暗示,关系应是相当亲密了。
那么,他的未来又当如何呢?
个人的行迹,早已汇入烟海。或许从宏观的角度,更能观想“老杜”们的命运。
在《铁西区》成片的2002年,工厂迎来了轰轰烈烈的“东搬西建”行动,将部分老企业迁至经济开发区,利用地价差获取资金,同时安置老员工,改造技术。一时间,如火如荼。
直到2012年,华晨宝马的铁西工厂正式开业,也逐步建成了度假酒店、商业广场、科技园区,曾经财政收入全市倒数第一的铁西区,得以重焕光彩。
所以,是生是死,是消逝还是新生,我们似乎永远无法看到终点。穷尽目力远眺,也不过历史的一处小小切片与断点。赛璐璐会破损,碟片会刮花,我们只能尽力描绘水中倒影,并将之向下传递。
这也是影像的价值所在。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